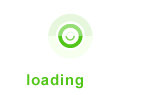似乎手头的事务总是琐碎繁杂,回头看看,过去受的那些磨难,走的那些弯路倒没什么,既是生活的谈资,又是经历的财富,也是一个少年从不识愁滋味的轻狂青涩成长的足迹。
刚从学习毕业时,总默念着那句挥斥豪酋,指点江山的诗文,恨不能生出翅膀去工作。当我背上换洗衣服、行李卷和派遣证,当月台上母亲和大姐的身影渐渐模糊直至消失,当我在一列列拥挤不堪、发馊怪味的车厢找不到座位,当火车穿越了隧道和黑夜之后,当短暂的兴奋被疲惫所拖垮,凌晨时分,大约两点,我终于到了目的地,陕南的西乡。
天飘着细雨,有点冷意,我背着行囊下了列车,并没有人接我。车站里那几盏路灯明晃晃的,有点刺眼,千万条细密的雨丝在光影之中飞散,南方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。我问了车站招待所,说在铁路对面。我扛起行李包裹,那是母亲为我缝制的一床新被褥,还有大姐塞给我的二百元钱和方便面、火腿肠。我和我的行李,连滚带爬地从一个车厢底翻过另一个车厢地,铁轨湿漉漉的、很冷,石渣硬硬的咯得人疼。雨一直下,八月的夜是如此的漆黑和冷寂,我记得翻了四股道火车,头上冒出汗来。我拍打招待所的门,服务员不耐烦地嚷嚷,轻点,又不是聋子?我自报家门,她给我说了几个房号。我又敲门,良久,陌生的人开启陌生的门。我迷迷糊糊地倒在一张床上,倒头就睡。
我睁开眼时,有人喊我去报道,上了二楼又下了二楼,公司的人事主任在楼下刷牙。他让我等会,就把我领去了工班。我背着行李跟在主任身后,他在钢轨间的枕木走着,如履平地。我顺着钢轨旁的石渣,大步快走却赶不上他的步点。从此,我进入了完全陌生的人群之中,开始了我独立的人生。我打电挂回家,母亲问怎么样,我说好。挂断电话后,我回想着那个“好”的回答,有点勉强,透露出少年的失望。
工班最初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,同宿舍的阿牛总是磨牙。起初,我以为是火车的声响,那是铁与铁碰撞才有的刺耳鸣叫,一夜未眠。让我很快融入工班的是那天中午的伙食,红烧茄子、小酥肉。烧菜的是四川师傅老李,他人高马大将军肚圆溜,看着他笑呵呵的样子和油光满面,让我胃口大开。我一口气吃了两碗米饭,满嘴的油汁和辣红。我开始这师傅那师傅的亲切叫着,买了饭盒,习惯了磨牙声,也翻开自考书写写画画。这时候有师傅嘿嘿笑说,一年师傅两年兄弟,三年就和师娘上了床。你们这些学生娃,没几天就骑到老子头上了。我无语,只得嘿嘿一笑。我和师傅们一起看碟,也聚众喝酒、打牌。啤酒、白酒不醉不休;扑克、麻将应有尽有。
当然,还有一起出工。我走在长长的铁道线上,明晃晃的钢轨延伸到山的尽头。西乡地处汉中盆地,地势还算平坦,远处是青出于蓝的山色,眼前水塘、稻田、屋舍如星辰随意洒落,路边碧水中有几尾曲项长歌的白鹅,荷叶翠绿,荷花红润,与一簇簇的灰色屋舍朦胧成江南的最初印象。
我背着铁锹、洋镐,手上起了茧子,说话也蹦出些脏字。第一个月开资,我领了九百八十多,那个高兴啊,飞流直下三千尺,扶摇直上入云天,我终于赚钱了。我拿出六百块钱寄到家里,花了50块钱买了电话卡。在邮局办完了这些事,给母亲报了喜,再摸口袋,剩下的300多块钱没了。同事说,怕是早让贼盯上了。天又飘起了小雨,我郁闷到极点,下午还要挖沟呢。
就这样我的工程生活开始了,那一年我十九岁。我的颌下冒出几根毛毛,公司发了电动剃须刀。我试了几次就收不住了,胡子如同雨后春笋,两天不刮就面目全非。第二年,我去了甘肃高台,在戈壁滩上领着民工挖电缆沟,干完活到小沙漠浪荡,看古长城的垛口、城墙浊蚀成废墟一片,也吃了林泽的小枣嘴角余香。工程开通当天,大雨滂沱,我缩成一团守在岗位上,远处的祁连山,雪色茫茫、连绵不绝,那份子清冷和妖娆铭刻在雨水湿透的心里。下半年我进了秦岭,在举世瞩目的秦岭隧道一侧的青岔车站,第一次当上技术员。白天,我土头灰脸地泡在工地,晚上在租来的民房里翻阅图纸、记工程日志。我们住的民房以前是个猪圈,喂猪的水泥槽道还在。有一天,风吹山谷、山雨倾盆,房顶上一坨瓦片带泥巴,砸在我的被子上。晚上回来,也顾不得被子被弄得黑乌,抱着图纸跑到房东面前,一顿吼叫,你看看你的破房子,连这点雨都遮不住,把我的蓝图全弄花了,这可咋办?
两年的工程生涯让我彻底了成了千百万的筑路大军中的一员,四海漂泊,工地为家。我们这帮子吃肉喝酒、叫爹骂娘,有时几句话不对口,免不了拳头相加,当时好像是杀父仇人一样,过几天又哥们弟兄的发烟敬酒。也有些奇人、怪才,有个师傅负责熬绝缘胶,脸被熏得结了一层黑茧,活脱脱的“黑油条”,到哪儿警察都要查身份证;可他收音机买了几十个,社会新闻记了一啰框。开资时,问他多少,他说管他呢?有人打趣女儿不是他亲生,他说管他呢?也有职工家属来探亲,众人就变着花样教坏小孩,你爸爸妈妈晚上干啥呢?我对一个五岁的小孩说,叔叔带你去玩。他犹豫了半天,说把我妈也带上,一群人都放肆得笑开了。工程队就是一个大家庭,有能掐会算的半仙,有谈了一连女朋友的帅哥,有踏实干活的小高,我完成了自学考试,算是给漫长的求学生涯画上一个句号。
第三年我去了新疆,从此和那种巨大的辽阔和包容结下不解之缘。进疆时到的是吐鲁番,吃的葡萄、哈密瓜皆为上品,路过达坂城也没有见到梳辫子的维吾尔姑娘,在天山北麓遭遇粗狂和苍凉。离开新疆是从阿拉山口走的,那里的风还是一年只刮一次,一次就从年头刮到年尾。虽然近在眼前,却没有去葡萄沟、艾比湖、赛里木湖,也包括几百米外的阿拉山口边防哨所,或是心情没有调试好,或是高负荷的施工打消了兴致。临走时,老维子技术员阿卜杜勒邀请我到他家,新疆拉条子款待,还送了库车小刀。验收单位的技术室主任是个高个子女的,老家浙江,请我吃两块钱一串的烤肉,管够。他们的领导问我想不想留下来,我摇摇头。
这期间我还去了甘肃、云南。在甘肃住在一个叫高阳的村委会内,因为一件小事和另一帮干工程的起了纠纷,洋镐把一人一把、随时准备拼命,想起来有点后怕。在云南深山,没有电,点起蜡烛;没有水,从山上挑来泉水。夜晚河流的湿气和水声爬到了枕边,我的腰就疼了半年。那三年的时间里,无论是新疆,还是甘肃、云南,都难得见到女孩,更别说恋爱了。与家的联系,不过是新疆的葡萄干、临泽的酒枣,云南的兰花草也挖了几株,不远千里的带回去。
都说一将成名万骨枯,工程结束,火车开行,作为铁路施工单位的公免也取消了。回头望去,那钢铁动脉有我洒下的汗水、泪水,那一个个远去的车站又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发丝和愁绪呢?向前走,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那么疲乏,还要打起精神啊,新的工程又要开始了。也有美好的事情,新疆的食物总是让人嘴馋,那里的米是长粒的,西红柿是鲜红的,水是雪化的,空气是纵横几千里自由飞翔的。
工程的繁忙是难以想象的,气温零下二十度,一段百十米的电缆沟,民工前后跑了十三个,最后一个说,给多少钱,我都不干,这要人命呢!我们的师傅、兄弟在地上生起火,一边烤地、一边烤手,八个人四天啃完了这一百多米。
山口大风起兮,卷着沙粒石子呼啸而来,我们则无言。那种风最可怕时,能把汽车打回白铁皮的原形,能把人直直地吹向墙壁摔成骨折。然而,风中的师傅,露出那黑亮的眼眸,给了我力量,让我走向了成熟。冬日里起风了,无论穿多厚的衣服,都像赤身一样。风是细细的刀子,蹿进脖子,钻进袖子,割得人肉生疼,然而我们挺住了,我们成功了。从新疆转移的时候,我对着远处的艾比湖说,我们还会回来的,不仅仅因为这里有一大帮朋友,更因为铁路还要延伸到更远更荒凉的地方。
工程的第六年和第七年,我转战南方在广梅汕铁路施工。我们住在河源,是一个新兴城市,历史却也悠久,当年秦国的大将军赵佗开疆拓土,史称南越王,河源火车站伫立着赵佗的马上雄姿。
记不清定测线路时,多少天毒日头下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行,九十五公里铁路也记不清用脚板丈量了多少遍。充满温情的回忆,是我们摘了老乡的几串桂圆,一边奔跑一边往嘴里塞。甘蔗林、香蕉地、青山无尽、河流绵长,青纱帐里的小睡,几个人就着矿泉水大嚼干饼子也是香甜的。我是工程部长,广州、惠州、河源、梅州、汕头来回颠簸,几乎踩成了胡同,也记不清走了多少次在车上草草吃饭。而最刻骨的是两次交工——
一次是五天五夜几乎不曾合眼,玩命样的抢工。我眼睛红得如同兔子,胡子也来不及刮黑旺旺的,我泡在配线柜前,一会是万用表,一会儿是电烙铁,看继电器的吸起和落下,比看到儿子出生的眼睛还直。完工当天,我直接进医院,躺在医院里输液,爱人来了五六个电话,我却在梦里庆祝着有惊无险的交工。
另一次是六十多个小时里睡了四个钟头吃了两餐饭,点灯熬夜,埋头苦干。交工并不顺利,业主的一个领导指着我鼻子,你不是说一点问题没有吗?逞什么能?当领导坐着车一个个走了,我枯坐在芭蕉树下,如此大的叶片,如此诗意的造型,我的泪水奔流直下,一颗一颗落在脚下的泥土里,悲伤汹涌成河。有师傅拍拍我的肩膀,我说,我没有打过败仗啊,我不服啊。
工程七年,我多少的欢笑和泪水留在了天南海北的铁路上,或许无言的钢轨记得,或许无数的道砟记得。在这七年里,我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青年,涉世之初的稚嫩变成了今日的成熟。我结了婚,也有了孩子,送走了母亲,又有多少悲伤和思念能用文字来书写呢?我在一个个工地的奔波和操劳,谁会记得,谁又会想起呢?
而我,不过才做了七年工程,如今暂时远离了工地。做那个决定时,我自己偷偷的哭了,我承认我不够坚强,常常把往事回想,把兄弟挂念,泪水会不争气的汩汩而出。那么,还有做了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工程人呢?我们这样到底为了谁呢?仅仅是工资高吗?我们的所得是不是和我们的付出一样多呢?无数次有人劝我离开,身边的同事也有出走的,而我依旧留了下来,这是为什么呢?
当那种不是常态的现实生活变成了一种常态的心灵归宿,当我们逐渐习惯了漂泊和艰苦的生活方式,当手上的工程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包含着更多的责任和情感,当很多东西无法理清、无法言表却又无法割舍,当咬牙切齿的怨恨中隐藏了深沉的爱和依恋,这一切怎么不让人崇敬,不让自己感动呢?有一种胸怀就是博大,有一种选择就是震撼。
多少年后你回头看时,现在的困境只不过是一支插曲,经历就是人生的财富。
可现在怎么办?我已经离开了奋斗七年的单位中铁一局,因为企业重组,我和我的同事们进入另一个全新的团队——中铁武汉电气化局
我望着蓝蓝的天,还得好好干啊。
——贾中华